摘要:“丧”成了新时代的朋克,在年轻人之间传播。生活已很不易,说点真话还不行吗?

大白天,两个高中男生坐在河边的石阶上聊天。
“明天有考试,好烦。”
“明明才到五月,好热。”
“这根薯条不会太长了吗?有这么大的土豆吗?”“有啊。”
这是日本 2016 年电影《濑户内海》里的一段场景,事实上,也可以说是所有场景——因为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在拍一件事情,都是濑户和内海(片名原意是狭窄海峡,电影里分别是两个男主的名字)一年四季坐在河边,纯聊天。
在旧有的“青春片”概念中,主角往往拥有满满的正能量,最后要实现一番“伟业”。但是《濑户内海》却讲述了两个再普通不过男生的另一种人生哲学——“青春为什么一定要跑步流汗,为什么就不能在河边虚度呢?”他们抱怨学校、偷瞄女孩、围观路人、吐槽父母……这些是他们享受青春的方式。
濑户和内海瘫倒在石阶上的样子,看起来很像国内大火的表情包“葛优瘫”。过去一年,20 多年前《我爱我家》中无赖的北京青年“季春生”,突然间被人们翻了出来,被用来表达着某种“生无可恋”的情绪。
不仅是他们。你可能早已发现,有越来越多拥有相同气质的影视、表情图、段子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它们从表面看起来,通常都带着颓废、沮丧、奇葩等消极情绪的特征,换句话说,是站在“积极向上”的反对面。然而这些曾经被视作“负面”的形象,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概括此类精髓的汉字——“丧”——在年轻人间流行了起来。

《濑户内海》
这一代焦虑的年轻人,把“丧”看作生活的真面目
就像“腐”一样,“丧”字起初被国内年轻人用起来,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有关。2005 年前后,日文中出现了“丧女”(モ女)这个说法。它和“干物女”近似,指的是“缺乏魅力的女性”「モテない女」。而“丧男”也指缺乏魅力的男性。
有不少部以“丧女”为主题的动漫作品。2011 年由二人组合“古川尼可”创作的漫画《我不受欢迎,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就描绘了一位社交障碍的女主角黑木智子。她在学校里饱受折磨,越想要让自己变得受欢迎,越容易成为一个笑话。
“丧”首先勾画出的,是一种失意者的形象:不顺利、不开心、无能为力……但事实上,相比带着“主角光环”的英雄们,这样的人物可能反倒更贴近生活中的大多数。
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发达国家严峻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年轻人们获得成功的机遇在减少。一些被称作“宽松时代”的日本年轻人,想要毫无压力地过着安稳的日子——但却依然遭遇到事业家业都不顺利的现实。
《濑户内海》的导演大森立嗣这么描绘过”濑户、内海们“的特征:“这些人物大多数在社会上碌碌无为,整天无所事事。看上去每天的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其实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们的笑脸背后隐藏着无尽的孤独。”
大森立嗣指出,此类形象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之一是“日本男权社会的衰弱”,“纵使你是一个大好男人,在这个现实社会中,依旧起不到什么作用。”

《丧女》
而同样作为“丧”的代表人物,美国动画剧集《马男波杰克》里“马头男身”的男主人公,被认为代表着“当代不快乐”的另一类典型——空虚的中产阶级。
在他 50 岁出头的年纪,波杰克过着狂野、富足而又空虚的生活,即便深知任自己挥霍的时间所剩无多,仍然以酗酒和沉溺女色来否认现实。他用贪婪的野心填满了内心的空洞,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又来了......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些事情会让我开心呢?”
这部剧的创作者拉斐尔·鲍勃·瓦克斯伯格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说,他的灵感来自于年轻时期那种“毫无头绪、但又自以为是”的焦虑。
在美国,“Y 一代”(70 年代末之后出生的人,又称为千禧世代、网络时代)被视作更注重个体价值、更加多元化的一代。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正在经历着更加严重的迷茫。
流行心理学网站“Wait But Why”创始人 Tim Urban 在《Why Generation Y Yuppies Are Unhappy》写到,这一代人的普遍性格特征之一是焦虑。有一条关于幸福感的公式是:“幸福=现实-期望”。而“Y 一代”的幸福感常为负数。他们见证了上一代人塑造的繁荣,很容易从小怀有夸张的期待和野心,但却在现实的挫折中陷入困惑。
波杰克的房客陶德是“千禧一代”的失败典型。他五年前就搬进了波杰克建在山上的“庞然怪屋”,整日游手好闲,除了吃早餐麦片就是抽大麻。配音演员艾伦·保罗说,陶德可能是“电视上第一个无性别的人物”,他对波杰克的忠诚最终总是被回以令人心碎的冷漠。
而在中国,那些坐在电脑屏幕前的观众,对角色们的焦虑能够感同身受。中国社科院去年 12 月份发布的《社会心态报告》显示,年轻人们的情况不算好。他们在大城市承担着工作、物质的压力,而回到小城市又承担不了复杂的人际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年轻人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这样的年轻观众们,对于粗暴的“成功学鸡汤”难以再买账。他们需要得到更加复杂的情绪内容。

《马男波杰克》
在激烈竞争的娱乐产业中,“丧”就是前卫
波杰克诞生于美国电视业的“峰值”时代。
2015 年洛杉矶的电视评论协会峰会中,FX 电视台的总裁 John Landgraf 首次使用了“PEAK TV”一词,形容高速增长的电视节目数量,已经快要触到市场容量的天花板。
美国电视业有三次公认的“黄金时代”:二战后、80 年代、以及 2000 年至今。最近十几年来,伴随着流媒体平台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发行网络的开拓,电视业持续壮大。每年都有大量不同类型的新电视节目被生产出来。
根据 FX 的统计,2006 年全美约有 192 档原创电视节目,到了 2015 年这个数字是 421 档,而 2016 年则一共有 455 档,十年间增长了 137%。 明年就很有可能突破 500 档。
“峰值”时代的直接结果,就是再没有一档中等的节目,能够轻易获得成功。为了争夺挑剔的观众们,制作公司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靠着模式化的既有经验来维持关注度,而必须投入更多去开发潮流。
美剧《黑客军团》为 USA 电视台拿到了去年的艾美奖。USA 在过去十年间依靠“晴空节目(总是将世界表现得晴空万里的,俗套化的探案集、鸡汤喜剧内容)”就能够获得好看的收视率,但如今为了吸引持续流失的年轻观众,他们必须做出改变。《黑客军团》这部剧集说的是黑客行为、数字生活的隔离效果等目前红极一时的主题,内容比此前所谓的“晴空节目”要阴暗得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想要在有线电视行业大赚一笔,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点,”决定投拍这部剧的 USA 负责人邦妮·海默说,“我们接受了我们不会得到大量奖项的这一事实。而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商业领域。如今的竞争已经不光是有线电视业务上的竞争,好内容也成了我们竞争的一大重点。”
当制作公司致力于摆脱“俗套”,曾经的小众被重视了起来。在过去的几年间,一批“另类人物”得以取得耀眼的成绩:抑郁的马男、《女子监狱》里的变性女犯人、《罪夜之奔》里倒霉的巴基斯坦裔学生、《伦敦生活》里在惨淡之中硬撑着假装不在乎的咖啡馆女老板、《我们这一天》里永远减不下来体重的女儿凯特……
其它竞争激烈的流行领域也是如此。日剧即使在“丧”的门类之中,也做到了不断推陈出新。
2015 年拿到学院奖最佳作品的《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男女主角分别是无法认同社会爱情观的刻板公务员女性以及二次元宅男。而双方结合的方式是通过相亲。
2016 年收视大获成功的《逃避可耻但有用》,讲述了一位大龄处男,和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女研究生,为了逃避彼此的问题,开始了一段“雇佣婚姻”。
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动漫界,热血少年也再也无法一统天下,取而代之的是为超能力苦恼的齐木楠雄、致郁的萝莉小圆、伤物语……去年大红大紫的新海诚,最擅长的就是少男少女之间的“小确丧”。
对于制作者来说,“丧”和“魔性”都一样是好用的“设定”,都能够带来新鲜感、话题度。

《秒速 5 厘米》
在社交网络上,“丧”就像新时代的朋克
在互联网上,情绪不仅通过完整的影像、文字传递,还可以通过一些碎片化的截图、段落扩散。
事实上,你可能还没有完整地看完一集波杰克,但只要你曾经刷到过朋友圈的某些截图,就已经能从台词字幕之中,理解到它的气质精髓,和志同道合的伙伴谈论了起来。
一些触动“丧”情绪点的表情动图,常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葛优瘫”、“青蛙 pepe”、“_(:з」∠)_”……当一个“热点”产生之后,微博微信上的“营销大号”,又会主动紧接着跟风创作。“葛优瘫”过后短时间内,各种类型的“XX 瘫”都冒了出来。
 葛优开腔拒谈“葛优瘫”
葛优开腔拒谈“葛优瘫”
同样是在社交平台上,一些率先说出“丧”态度的人获得了粉丝。
“曾良君”是“90 年生人,建筑系学生”。他从 2011 年开始在豆瓣、微博、犀牛故事、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发布文章,撰写一些“反成功学”的图文段子。
他的语录流传开来:“一个在家里看电视喝饮料吃零食的人,虽然对社会贡献不了什么,但也没有危害啊! ”“每当作业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突然充满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轻人喜欢“葛优瘫”、“曾良君”的原因,是因为“真不想学习/工作啊”真的是他们的日常吐槽,是和刻板教育不同的一种声音——而后者的固定表现,就像另一位网友 @轩介 所说:“用长辈的话来总结这日记,你有这么多闲功夫写这些还配些不三不四的图,作业早做完了。”
在每个时代,青年文化都是最喧嚣、最活跃的一拨。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些反传统的、情绪浓烈的、带着夸张特质的信息能够最先被注意到,然后被放大、扩散。某种程度上,如今的弹幕网站、微信群/小组等等,就像是曾经让 60、70 年代青年们聚集在一起的酒吧、俱乐部。
我们曾经在介绍朋克文化的文章里提到过,受到中产消费文化的影响,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推崇表达愤怒。与曾经的嬉皮士、摇滚青年相比,包括“丧”在内的青春文化都显得更加柔和。但是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渠道下,原本边缘化的“亚文化”面前少了障碍。他们能够迅速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传播他们所认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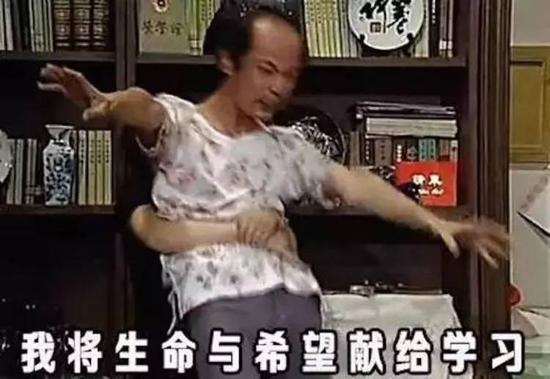
生产“丧”,如同生产“正能量”一样
《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上海彩虹合唱团继今年年初那首《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之后,第二首走红的原创“神曲”。歌里唱的是城市里常态的加班场景:“有一个老板/叫做大卫/下午六点出现眼神恰似黑背/手里端着一壶热腾腾的咖啡/嘿嘿嘿/我们要不要来开个会。"
彩虹合唱团团长、词曲作者/指挥金承志告诉《好奇心日报》,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朋友圈里“加班狗”的抱怨。
但是当被问到这首歌是否属于“传播负能量”的时候,他认为答案是相反的,这首歌最重要的一点仍然就是“正能量”:“前几天某个电影公司的老板跟我说,城市生活太沉重了,我们需要幽默感。我觉得,现在大家连吐槽都是满怀戾气,啊——!我个人觉得说不至于此。我们生活是真实的,你不可能拿着斧头砍人,这个东西很无用,但是听完这个音乐能留下热泪的话,其实是一种抚慰吧,听众宣泄了情绪,那我们的社会功能也就达到了。”
其实回顾那些关于“丧”的流行,你就会发现人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情绪宣泄口,他们最终寻求的还是慰藉,以及解决问题的动力。
在虚拟世界里,那些闷闷不乐的人其实都充满魅力,满怀友善。濑户和内海珍惜着和彼此的“一期一会”。波杰克无非是个渴望被爱的混蛋。曾良君写着“不想努力”的帖子,出了三本书。
而当回来讨论现实生活时,失败终究是无可奈何、不受欢迎的。大家拥抱它,但希望把它留在虚拟世界里。
生活的艰难一如既往,不管是治愈、玛丽苏还是丧,都不过是鼓励前行的办法而已。

《伦敦生活》
本文著作权归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周刊(微信ID:CBNWeekly2008)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新浪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