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文共6528字,阅读全文大约需要10分钟。在这篇文章里你将看到:中国约有1400万名“同妻”,这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同妻”多的原因在于,社会的舆论还没有达到接受同性恋同居或不婚的程度。同妻是一个弱势群体造就的另一个弱势群体。
今年是李洁结婚的第十年,她正在第二次起诉离婚,理由是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
刚认识丈夫的时候,她觉得他“很安静、体贴、踏实,从不会和你吵架”,因此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几个月后便怀了孕。但丈夫虽然对她很好,却有些不对劲:他很少在家里洗澡,但是身上不脏,手机定位里有在宾馆的记录;但是在李洁的直觉里,自己的丈夫“不会和一个女人开房”,因为他好像对女人并不感兴趣。
后来,李洁逐渐发现另一些现象:丈夫似乎经常便血,厕所里擦过的卫生纸经常带着血;两人虽然有性生活,但是在性生活的过程中,丈夫从来不脱上衣,也不会触碰到她的上半身,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机械性地完成任务。
当李洁找到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咨询时,张北川告诉她,可以基本确定她的丈夫就是同性恋。
像李洁这样的人,在中国被称为“同妻”。同妻特指与男同性恋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广义上也包括前同妻、同女友(刘冬&唐魁玉,2014)。2015年,张北川主要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潘绥铭2010年对中国成年人口的多层等概率性学抽样调查给出的相关数据,估测我国男同性恋者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2100万,配偶是男同性恋的女性人口数约为1360万(张北川告诉KY,1360万是与初婚男同结婚的女性数量,如果算上有婚史的,应在1400万以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的估计是,在中国男同性恋者中,有90%以上的人会选择结婚,其中80%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张晔,2012)。
然而,极少有同妻像李洁这样决心摆脱婚姻,大多数人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中,和同性恋的丈夫维持着婚姻,维持着无性或者很少的、工具性的性生活。而无论是否离婚,她们都经历了人生中最困难的精神冲击、价值观和人生意义重塑的挑战。
201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唐魁玉的课题组开始将同妻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进行研究。当时,他曾受到社会学家景天魁的鼓励,但对方同时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同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唐魁玉认为,“相比残疾人等身体上的弱势群体,同妻更是心理上的弱势群体,她们心理痛苦、身心俱疲但不容易摆脱,困境特点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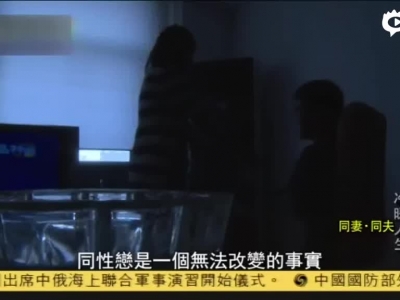 同妻同夫:我们希望法律保护我们
同妻同夫:我们希望法律保护我们
KY经过对当事人和专家的采访,试图走近这个人群,还原她们的故事,并探讨这一现象。

2016年1月27日,山西霍州。玉梅和丈夫结婚15年,育有两子。得知丈夫曾把同性恋人带回家后,她近乎崩溃。为了不让外人到访,她故意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群体
社会学家李银河(2009)提出,在国外虽然也有类似的问题(同妻/同夫被称为Straight Spouse),但在西方,只有约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是已婚者,同妻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
李银河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同妻”多的原因在于,社会的舆论还没有达到接受同性恋同居或不婚的程度。同性恋迫于“男大当婚”以及传宗接代的文化压力,大多会选择进入异性婚姻生活。(此处特指西方国家,在穆斯林国家、印度、非洲的部分地区,同妻现象可能更加严重。)
尽管同性恋已经在199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疾病中除名,2001年,我国也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认定,同性恋性取向不是疾病,只有在同性恋性行为导致了心理冲突、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才可以称为性心理障碍;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仍然相当有限。例如,今年5月,就出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由于医院强制让他打针、吃药进行“扭转治疗”,河南驻马店的男同性恋者余虎起诉驻马店精神病院。
在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同性恋者中,“出柜”的仍是极少数,多数同性恋者选择了隐瞒,他们进入了婚姻。
唐魁玉认为,导致同妻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爱情与婚姻的结合度低。在西方国家,爱情和婚姻往往是高度结合的,人们更希望婚姻关系是有爱情支撑的,亲密度是令双方个体满意的,他们不太会为了家庭的完整或者孩子的需要而维持一段婚姻。
因此,一方面,西方国家很多人(一些宗教信徒除外)在婚前已经经历过性生活,同志身份不容易在婚前隐藏。而另一方面,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同妻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往往相对比较短暂,在婚后如果发现伴侣是同性恋的事实,多数人会选择很快离婚。
“西方重视个人的权利,而中国重视家庭。”在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在张北川还是唐魁玉的研究案例里,像李洁那样坚决选择离婚的少之又少。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考虑到家庭和孩子等多方面的原因,同妻在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实后,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婚姻中。
与城市里拥有更成熟的同志社区和文化相比,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同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农村的同性恋男性更容易选择离家外出打工,在陌生的环境中寻找约会的机会;而农村女性则经济条件更差,对同性恋的认识更少,更难以识别和应对,也更难以通过信息渠道获取帮助资源。
李洁自认为属于同妻中少有的“财务自由、内心强大的人”,经过多年的个人努力,李洁事业有成,收入是丈夫的10倍以上。“但是在这个(离婚的)过程中,我受的伤害仍然很大,仍然举步维艰。”李洁说,“可想而知其他女人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2015年10月31日,张秀丽已经和丈夫分床睡了很多年。维持家庭的唯一出发点是孩子。
一种痛苦引发的另一种痛苦
68岁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曾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张北川已经坚持了十余年的同妻研究。他原本的研究对象是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弱势群体;后来他发现,同妻更是弱势群体——这是一个弱势群体产生的另一个弱势群体,一种痛苦引发的另一种痛苦。
但他坚持认为,尽管丈夫本身也是受害者,但在这段关系里,妻子是更大的受害者,而丈夫则是施害者,他曾被一名青岛的同妻诘问:“哪有让受害者同情害人者的?”
“结婚,只是借个肚子用一下”
和李洁一样,王娟在婚姻里从来没有真正可以称之为“亲密”的感受。丈夫和她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每天都是头朝着不同的方向睡觉;有孩子以后,他便每天都把孩子隔在两人中间睡。在婚后,二人就开始努力怀孕,并生下了两个孩子,之后便再也没有了性生活。
王娟丈夫的行为,在同性恋丈夫中非常典型:在大量的同妻案例中,妻子的意义除了在于掩人耳目,更重要的在于传宗接代。因此,一结婚就努力怀孕,比如算好排卵期,只在那几天选择和妻子同房;性行为非常机械,没有前戏;在完成生育任务后立刻中止性行为——这都是同性恋丈夫的一些常见的表现。
“有的丈夫会说,结婚,不过是借个肚子用一下。”张北川说,“这是没有把女人当成人来看。”
由于同性恋男性对于女性没有性需求和唤起,他们在面对妻子时经常会遇到“硬不起来”的问题。2000年加入张北川工作室的王娜说,为了能够传宗接代,他们有很多种应对方法,比如服用伟哥、利用晨勃进行性行为,或者先自我刺激,勃起之后再进行性行为;或者“关上灯,把女人想象成男人”。
但这样的方法也并不总是奏效,尤其是到了婚姻后期。王娟和丈夫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是男孩,但男孩在3岁时患病夭折。之后,她还想再努力生一个儿子,但尽管精心准备,丈夫却“无论如何也硬不起来了”。
在唐魁玉的研究中,长期缺乏感情的、工具性的性生活,会让几乎所有的同妻都会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定位。有同妻这样描述:“我问他你是不是婚前就确定自己是同性恋,他说是的。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他说他喜欢孩子,他需要一个家,需要一个人为他洗衣服做饭生孩子,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她们会逐渐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伴侣为了掩饰性取向和生儿育女的工具。尤其是一些遭受伴侣情绪虐待和家庭暴力的同妻,在得知自己的婚姻是一场谎言之后,会对自己的身份和婚姻产生深深的质疑。

2016年1月31日,山西太原,三年前发现丈夫的同志身份后,她常常在深夜被惊醒,然后在房间踱步至天亮。
“我是个双性恋”,“我会改”
王薇险些成为同妻。在结婚的最后关头,男人退缩了,说自己有艾滋病。她不信,反复追问,并且表示即便对方有艾滋病,也愿意和他在一起。男人无奈,才承认了自己是个同性恋的事实。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王薇这样幸运。在张北川的案例中,几乎所有的同妻都在恋爱和婚姻中经历了长期的被欺骗,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十年。一些丈夫会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或者谎称在婚前没有发现。
而且,即便是在被发现确凿的证据以后,欺骗仍然存在着。很多丈夫选择不承认,他们往往说是双性恋,或者自己“会改”。
王娟曾经相信过自己的丈夫。秘密是被他们的女儿发现的,女儿翻看爸爸手机时,告诉妈妈里面有“奇怪的东西”;当王娟打开手机,发现自己的丈夫在和一个50多岁的男人调情,互相发自己的生殖器图片,丈夫还告诉对方,我从来都对女的没兴趣,只对男的有兴趣。有些话她看不懂,比如丈夫说自己“是0.5,可攻可受”。
当时,不敢相信的王娟去问丈夫:“我和你同村,从小学我们就是同学,你为什么要这么骗我呢?”丈夫回答说,自己是双性恋,是婚后才发现的;并且“他可以改”。
他们真的是双性恋吗?“在我们这里见得太多了,很多同性恋丈夫会用双性恋作为遁词。”张北川说,宣称自己是双性恋是一种很典型的欺骗。但在这些案例中,真正的双性恋非常少,他们往往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兴趣。
然而,由于妻子往往也缺乏对同性恋的基本了解,这可能会使她们对此抱有希望。她们希望能够通过“治疗”,来“修正”伴侣的性倾向。在张北川接触的同妻中,很多人都会询问,同性恋怎么才能改成异性恋?有人说,自己在百度上查到很多网页都写着“矫正同性恋”,应不应该相信?
唐魁玉的博士生刘冬说,妻子对同性恋的认识和认同,是同妻在婚姻中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在接触大量同妻的过程中,让她震惊的是很多同妻对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向的不了解和不认同。“很多人对同性恋的印象非常初级,很有可能来自影视作品,比如认为同性恋就是很娘娘腔的形象。”同妻对同性恋的认识不足、对同性恋的否定,也使得她们很容易厌恶自己同妻的身份。

关于丈夫的性取向,玉梅告知过亲友,对外却讳莫如深。
HIV和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在李明慧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的时候,她已经感染上了梅毒,传染给她梅毒的是她的丈夫,她后来才知道,丈夫同时也是HIV的携带者。随着丈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梅毒导致了脑出血,从一只耳朵失聪,到丧失了说话和行动的能力。最后,家里花光了住院的钱,她只能把丈夫带回家,每天晚上检查他是否还有呼吸,直至他在去年死去。
相比于阴道性交而言,肛交性行为在性传播疾病、HIV上的易感性更高,因为肛交易造成肛门破损,且直肠更容易吸收液体。这使得和他们有性接触的同妻也成为高危人群,而且在两性性行为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保护措施,女性的生理构造是感染病毒的温床。2011 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中国艾滋病状况的报告显示,婚内配偶的艾滋病传染比例正不断增高,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已将“同妻”列入艾滋病易感人群。
唐魁玉的学生宋懿(2014)在对同妻未来感染艾滋病可能性的考查中,120 名被调查的同妻中有 14 人确认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数量占总人数的11.6%;而在剩余的 106 位未感染艾滋病的同妻中,76 名同妻对感染艾滋病一事表示不知道或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上艾滋病,这意味着多数同妻还没有形成对艾滋病系统的防范意识。张北川则提到,在一项针对11名同妻的调查中,有10个人都从丈夫那里感染了性病,7个人感染HIV病毒,只有一个人没有感染性病和HIV。
而且,有一部分同妻也会在丈夫的要求下采取肛交行为,张北川认为,这是因为同性恋男性更习惯肛交的性交方式,且括约肌更紧,更易引发性兴奋。
(不过,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尽管肛交行为容易传播疾病,但这只是病理层面的表述,绝不是将“同性恋者”和“性病传播者”挂钩,或者歧视同性恋者、性病和HIV病毒携带者;而且,防范措施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病毒传播几率。
此外,HIV病毒携带者并不等于艾滋病患者,如果通过有效的抗逆转录治疗,HIV病毒携带者可以使血液中的病毒控制在不被检测到的水平,不但可以和HIV病毒共同存活几十年,而且即便在无安全套的情况下也不会传染给他人。)

张秀丽拿着从家里翻出来的丈夫的性用品。有次她带孩子外出,回来便发现了避孕套和润滑剂,她问丈夫是不是带人回来了,丈夫不回答。
丈夫是同性恋,令我感到羞耻
比起可能的健康风险,精神的痛苦则是每个同妻都要面对的。
美国的“同妻”咨询师、《同性恋丈夫检查清单》的作者Bonnie Kaye(2011)总结道,同妻在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后,心理的历程很像丧失与哀恸发生之后的6阶段:否认与震惊、愤怒与怨恨、讨价还价、退却与抑郁、接受以及拓展。
像李洁一样,当证据出现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否定和不相信。尽管她始终感受不到亲密,但是在这段婚姻中,丈夫一直对她很“好”。他们住在复式的房子里,她在楼上说自己口渴了,丈夫都会高高兴兴地去楼下帮她倒水;冬天开车时,她因为太累,都是开到楼下让丈夫去停到停车场里。而突然,她需要接受这个事实:丈夫从来没有爱过她,而且也不可能爱她。
在李洁度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她曾经一度觉得自己“失心疯”了。她长期在工作中走神、茶饭不思,最后因为抑郁症,她去北大六院诊治。直到在那里找到一名在同性恋咨询方面经验丰富的教授,向他描述丈夫的种种行为时,她仍然在询问教授:我的丈夫真的是同性恋吗?
在同妻的心理状态中,羞耻感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田欣(2014)说,和那些丈夫出轨其他女性的女人相比,大部分同妻表示自己更弱势,因为丈夫“出柜”更让她们感到羞耻。婚姻生活中性和爱情的缺失,丈夫的同性恋身份,让她们对自己作为女性的魅力和价值产生了怀疑。而且,一些人会将伴侣的同性恋归于自己的责任,认为如果她能做一个更好的母亲或妻子、或者是一个更有魅力更性感的女人的话,也许就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2014年6月27日,河北保定。在发现丈夫的聊天记录后,胭脂歇斯底里地摔碎了丈夫的电脑和手机。
比起社会和法律资源,同妻更多地依靠自助和互助
在唐魁玉看来,在社会和法律层面上,同妻可以接受到的帮助还很少。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而在目前的同性恋离婚案件审理中,他们还需要用其他的证据来实现婚姻的解体,“就像夫妻因为性关系不和谐而离婚,往往会说‘性格不合’一样。”
相较于较少的社会资源来说,同妻本身的封闭和不主动成为了更大的阻碍,援助组织或志愿者往往很难找到她们,而她们也只有在极度绝望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寻求帮助。
就目前来说,改变现状更多地还在依靠当事人自己的努力。QQ群等形式的同妻互助小组尽管刚刚起步,但其力量虽然正在逐渐发挥出来。
2011年,作为受害者的萧瑶在QQ群的基础上,建立了“同妻家园网”,注册人数一度达到4000人,使得中国的“同妻”现象开始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但网站最后被萧瑶的合伙人利用,以收取“心理咨询费”等方式诈骗现金9万余元,加上被一些男同性恋狙击,最终网站在争议中关闭。
如今,豆瓣的“同妻在行动”小组里也有四千多名成员。她们在小组里连载同妻志愿者手记,分享自助类的文章,发起线下活动。同妻们的行动也还得到了一些男同性恋者的支持,他们在豆瓣发起线上的支持活动,提出了“消灭未来同妻,我不骗婚我骄傲”的口号;在微博上,“我是同性恋,我不会和异性结婚”的标签已有820万阅读量。

2015年,福建泉州一家同志酒吧,曾是受害者的小德兰带着上百盒安全套前来发放,并做艾滋病干预。
同妻现象的背后,仍然有着性别歧视的影响
对于慕名而来的来访者,张北川总是建议她们先去检测是否有感染HIV,然后建议她们离婚,去寻找新的感情。然而,目前除了部分同妻会坚决选择离婚外,相当数量的人还在努力维系,或者试图重新构造婚姻。
在唐魁玉的研究中,有人是因为无法抛弃过去曾经的付出;有人迫于经济的压力;有孩子的家庭都会提到担心影响孩子;有的会同情伴侣;有人碍于面子。王娜说,有的当事人自己是同妻,发现身边的亲人(表妹)也是同妻,但是为了维护家庭、保持形象,她们彼此之间不会点破。
有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在离婚后去青岛找张北川咨询,原因是自己很困扰,每约会一个男人都不知道如何和对方解释,自己为什么既有婚史,又还是个处女。
对于少数选择离婚的同妻来说,离开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的。她们中的许多人耗费几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时间,其间经历丈夫及其家人的污蔑、欺骗和家庭暴力。李洁的丈夫在她起诉离婚之后,发现她去意已决,便开始打骂她,并以孩子作为要挟,提出房子、汽车、100万现金作为离婚条件,并且让李洁公开道歉,说明他不是同性恋。李洁觉得这很讽刺:“我经济独立,却因此受到了要挟。”
在刚开始做同妻研究时,刘冬觉得自己还很天真,因为她无法理解:这些人这么痛苦,为什么不离婚啊?
直到有一名同妻的话给了她很大启示。那名同妻说,“我如果离婚再找,可能只能找一个二婚的;而他不一样,很容易再骗一个大姑娘,给他生孩子。如果有下辈子的话,真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哪怕我是个同性恋呢,也不用遭这么多罪。”
刘冬开始觉得,同妻的问题不完全是同性恋/异性恋的性取向问题,同妻之所以会面临这么困难的处境,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源于男性/女性的性别问题。在婚恋市场上,一个离异的男性,要比女性受欢迎许多,女性离婚的成本更高。
经过了三四年的同妻研究后,唐魁玉、于慧也开始将“同夫”(与女同性恋结婚的男异性恋)纳入研究范围。但他们也认为,总体来说,与同妻相比,同夫的婚姻存续时间更短,这是因为男性摆脱婚姻的能力更强,在离婚后再婚的难度更低;而且,在同夫的婚姻中伴侣的性行为更多,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中双性恋比例更高,也可能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
刘冬认为,对同性恋的社会接受度的提高甚至同性恋合法化可以减少同妻现象,但不能消除,因为如果要提升同妻群体的地位,改变她们的现状,更根本地还在于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KY公开支持多元文化、始终支持LGBTQ人群权益。正如文中提到的,我们认为,同妻是一个弱势群体造就的另一个弱势群体,是一种悲剧造成的另一种悲剧。追根溯源,我们并不认为同性恋取向是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人性中的恶-欺骗、利用;社会对同志人群的不接纳;社会对于不婚人群的不接纳-婚姻在社会中不可撼动的正义地位;女性本身的弱势地位等;共同造就了这样的悲剧。
社会要为人们创造说真话、做真我的空间。而这个社会不是别人,正是你我。

玉梅与儿子站在窗前,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身份。她无数次想过离婚,但为了维护孩子的名声,她想要等到儿子上高中或大学以后。
本文配图摄影师赵赫廷,文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本文著作权归微信公众号KnowYourself(微信ID:knowyourself2015)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新浪新闻客户端。



